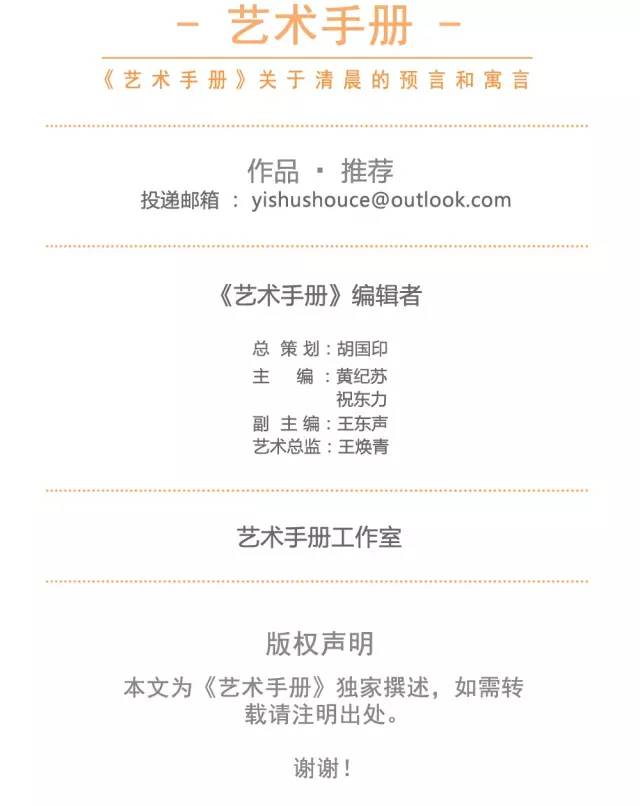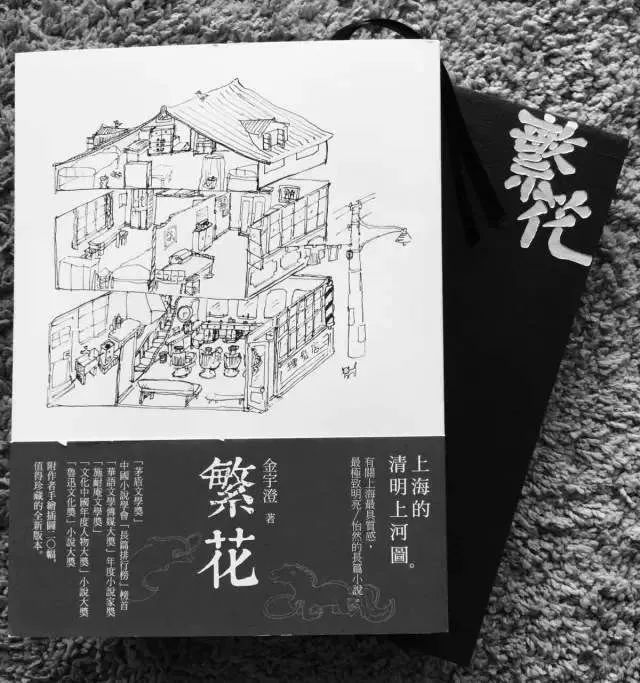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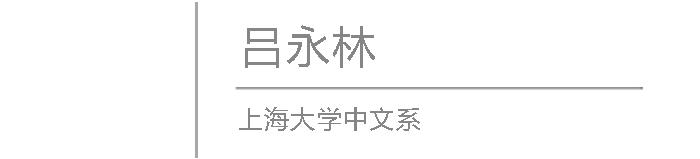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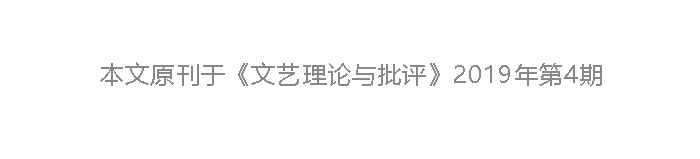
1990年底,《花城》杂志发表了王朔的《给我顶住》,小说写男主人公方言利用女友赵蕾及同事关山平,“费尽心机”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圈套,在妻子周瑾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成全”了她与关山平的“爱情”,最后,当作品内外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承受具体的故事结局和人生限定之时,方言却以失踪者的形象弃众人——包括后来“疯了似的在全城找了他很多天”的赵蕾——而去,从而将个人的未来投进某种不确定之中。及至作品终了处,已是方言失踪一年后的某个秋日傍晚,周瑾和关山平也已育有一女,三口之家,一派其乐融融的温良景象。值此刹那,“幸福”的周瑾“显得丰满、漂亮、容光焕发”,而关山平则向她道出了真相,原来他们此间的幸福,多半得归功于方言“精心策划”的“成全”。紧接着,周瑾和关山平有一段仿佛凝视着身边世界和无限远方的对话: “他想干嘛这个方言?”“往好处说,大概和我都是一样,幻想某种奇遇,生活一下完美无缺了。”“可能吗?你说他能得到吗?”“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我相信他只不过是换了个环境换了一些人但肯定还过着和这儿同样的生活。”“你说有么?那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的、人所期冀的……”“我说不上,一般的幸福感受我想是有的。譬如我们……现在……”1 作为一名读者,我已同1990年相隔甚远,但每次重读王朔的这篇《给我顶住》,心内总会生出一股颇为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我想知道,那个以“无形”之身奔赴“乌有”之乡的方言,后来究竟怎么样了?一方面我已了然,当这部小说被公开发表之时,某种曾经在80年代中国人身上广泛存在过的东西也已大面积“失踪”,许许多多的中年人,甚至青年人,都开始像关山平一样,不再对未来和远方怀有什么特别期待,更确切地说,是不再对那些涉及人的生活总体性的“奇遇”怀有期待。有意思的是,2012年,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出版,末尾处也有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沪生说,我一直听玲子讲,阿宝比较怪,一辈子一声不响,也不结婚,皮笑肉不笑,要么讲戏话,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说,一样的,玲子也问过我,讲沪生这个男人,一直不离婚,只是笑笑,要么讲,“人们不禁要问”,文革腔,玲子完全不了解,搞不懂沪生心理,到底想啥呢。沪生笑笑不响。阿宝说,我当时就告诉玲子,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2 此番谈话,若与关山平和周瑾那段对话并置,我们会发现,两段对话尽管在“发表”时间上相隔多年,意指上却有着契合之处。20多年前,王朔让关山平说:“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20多年后,金宇澄叫阿宝说:“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依据文本细节,我们基本可以辨识出,关山平所说的“这世界”是指80年代中后期或者再晚些时候的中国社会,而阿宝所说的“这个社会”则指90年代前期的中国社会。可问题是,如果有读者说,关山平和阿宝所言岂不也是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学写照!又如果,这样的读者还不在少数,那我们就有必要往深远处和幽微里追究一下,比如以某种精神分析学的方式去考量:失踪了的方言心中所求究竟是什么?一直留在此间的阿宝会不会是另一个方言?关山平当时是怎么做到放弃对“奇遇”的“幻想”的?方言又因何做不到,进而选择失踪的?在阿宝长时间的“一声不响”里,到底埋伏着怎样的精神搏斗?如今在我们身边,数不清的生命个体在心灵上又同方言、阿宝和关山平们有着怎样的映照关系?在这无数人当中,谁会是阿宝?谁是关山平?谁是方言?我们所属的时代和方言、阿宝们各自所属的时代是同一时代吗?阅读方言、关山平和阿宝们,是否就是阅读我们自己?阅读这些文学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否就是阅读我们自己的时代?是否还有生命的超越性在部分人的身上存活?如果有,这超越性是什么?它在我们时代和未来还有没有被普遍“现实化”的可能?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的种种欲望,其“精神本质”在于“重新建立原初的满足情境”3,这一“原初”,可被追溯至个人或人类的童年时期,因而在欲望满足的意义上,奔赴未来就是重建过去。这一理论假设,常常在作家们创造的文本世界中得以形象化呈现,无论他们本人对此是否自觉,也无论他们是在“纪实”还是“虚构”。譬如,《繁花》第一章(在“引子”之后)开篇处就有这样一段文字: 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头发飞舞。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4 毫无疑问,这是阿宝童年时的爱情,也是他终生难忘的“记忆形象”——或者说“原初的满足情境”。在《繁花》中,对某种“美而且好”5的爱欲对象的长久寻找,是阿宝一直不曾断绝的人生执念,但在现实中,这同时也是其持续不愈的“心病”,而那个“文革”期间失踪的邻家女孩蓓蒂,正是阿宝记忆中的“原型”式爱欲对象,至于其青年时代和中年之后的两次恋爱,则无异于其重建“原初的满足情境”的尝试。但这里面还潜伏着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无论是《繁花》中人,还是读者,往往都会将注意力投放到蓓蒂身上,却无视蓓蒂身旁或四周,还弥漫着阿宝的另一种爱情。换个说法就是,在《繁花》中,除了蓓蒂等人,还有一个阿宝的爱欲对象隐而未彰,那便是童年阿宝在屋顶上所眺望的世界及其未来。在那个归属于童年的“屋顶”时刻,所有挟带着强大异化力量的他者尚未给处于天真状态的阿宝带来什么创伤,主体和客体、自我和他人还处于一个短暂的和平之中,没有发生巨大断裂。因此,远声近影所触发和编织的,恰是眺望、想象中的朦胧家园,彼时的上海城市日常景象之所以能够“抚慰”童年阿宝的“胸怀”,就在于他当时对整个世界怀揣着爱情。无论小说人物和作家对以上问题是否足够自觉,那一“天真”时代的片刻“美好”,已于无形间构筑起阿宝心中理想的生命图景和精神镜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了成年阿宝“一辈子一声不响”的根由,以及他所谓“奇迹”的出处:唯有心中理想的“人”和“世界”同在,其爱欲内核才可能充实。“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东南风一劲,听见黄浦江船鸣”,独此两端俱全,才是阿宝真正想要重建的“原初的满足情境”,也才是他有意无意间最为远大的爱欲抱负。对于这样的心灵隐秘,“夜东京”女老板玲子又如何能理会得到。当然,在世界作为爱欲对象的维度上,童年阿宝所怀揣的基本还是一种较为抽象的爱情,因为他所欲望的“世界”,多半还停留在想象之中。后来,“文革”发生,在阿宝那里,它径直导致了种种劫难与创伤,其中之一,便是少女蓓蒂的莫名失踪——这是一个贯穿《繁花》全书的创伤性隐喻。青年阿宝,成为消沉者阿宝,就其个人而言,同时消沉的还有他在童年时代眺望过的世界。如今,作为一名青年工人,阿宝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十分压抑,数年之内,他和他的家庭也一直处于革命年代阴郁灰暗的角落里,小说中灼灼如焰的电车售票员雪芝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雪芝人极美,性情和志趣也同青年阿宝多有投合,这些似乎都恰好绽放在阿宝所欲之“美而且好”的道路上: 阿宝觉得,眼前的雪芝,清幽出尘,灵心慧舌,等于一枝白梅。两个人讲来讲去,毫不拘束。6 然而,雪芝之“好”其实有限,同许多人一样,她也不过是现实的顺从者。因此最终,“美而且好”的雪芝被阿宝父亲的政治遗留问题、阿宝工作单位的非全民性质、阿宝家窘迫的住房条件,以及她家人的反对等困难拘禁起来,动弹不得。我们看到二人分别时,有这样一段情景: 两个人,慢慢走到电车终点站,阿宝送雪芝上车,走了几步,阿宝回头,见雪芝靠了车门,眼睛看过来。阿宝不再回头,独自朝三官堂桥方向走。此刻,阿宝听见雪芝跑过来说,阿宝,我根本不怕爸爸,我会一辈子跟定阿宝,一辈子,真的。雪芝奔过来,一把抱紧阿宝。但阿宝明白,雪芝只是靠紧车门,一动不动,目送阿宝慢慢离开,雪芝的冲动与动作,是幻觉。……62路终点站,停了一部空车,张开漆黑大口,可以囫囵吞进阿宝,远远离开……7 一个犹在成长中的青年,遭遇其跟世界和他人之爱的两重破灭,被苦恼囫囵吞没,此乃阿宝终生待恤的创伤记忆。在雪芝这里,一旦选择放弃,她身上的“好”就脱落了,她的“美”自然也成了远隔之物: 雪芝背了光,回首凝眸,窈窕通明,楚楚夺目,穿一件织锦缎棉袄,袖笼与前胸,留有整齐折痕,是箱子里的过年衣裳,蓝底子夹金,红,黄,紫,绿花草图案,景泰蓝的气质,洒满阳光金星。……阳光照进来,雪芝身体一移,绛年玉貌,袄色变成宝蓝,深蓝,瞬息间披霞带彩,然后与窗外阳光一样,慢慢熄灭,暗淡。8 自此,雪芝与阿宝无关。同时,在读者眼里,雪芝美归美,但与奋力撞开未来新生的微观革命和创造无关,也与各种朝向“拯救”或“超越”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爱情故事无关。更准确地说,对于阿宝,雪芝的强大生产力其实是以一种消极、负数的形式显现的,正是她和“革命年代”一起,构成了成年阿宝最深刻的精神起源。

在阿宝的爱欲史上,第三位“美而且好”的恋人出现时,已是90年代。这个“美而且好”的爱欲对象,便是李李。李李跟阿宝的相遇,实际上是两个心头带伤之人的孤独相遇。李李之伤,在于家庭和世界的种种“无情”,包括她因雇人用混凝土浇杀小芙蓉而生的负罪感,虽然身上被人刺绘的血红“玫瑰”图案和英文字样已用医疗激光祛除,但其心里的血红“玫瑰”一直还在。因此李李所求,乃为世界或某人之“有情”,以容纳和消化自己巨大的创伤记忆。而阿宝之伤,则在于其孜孜以求的“美而且好”的爱欲对象一再失去——蓓蒂是失踪或死亡,雪芝是家人禁绝,同时,还有自己童年时所希冀的世界图景的幻灭。可以说,李李跟阿宝的相遇,骨子里是两个互为求助者与疗伤者的成年人的相遇。凡拯救必有障碍,对于中年阿宝与李李来说,最广漠、阴沉的障碍来自于时代。而在90年代的各路欢场之上,一种由成年人主导的“风月”文化正在将少年式的“爱情”扫荡得四下飘零,倒卖高档钻石的丽丽曾一言以蔽之地说,“这个世界,虚来虚去,全靠做门面”;“夜东京”女老板玲子认定,如今到处只见“胡天野地场面”,“样样事体,不可以当真”。9原本让读者们怀有期待的陶陶与小琴,就不幸被言中,他俩的情爱故事最后连一场像样的悲剧都算不上,小琴意外坠亡之后留下的,不是可以让陶陶追忆此生的挚爱真情,而是算计和欺骗,以致陶陶被闷得喘不过气来,心生恍惚——“此刻究竟几点钟,是哪一个世道”10。因此,中年阿宝和李李要想相互成功救治,成为时代的例外,就不仅得两个人同时“当真”,而且得两个人共同“确信”这世上还有他们所期待的“奇迹”存在。可惜,到最后关头,二人还是各自被某种“不确信”所裹挟,李李因不确信阿宝的决心,便拿新加坡男来作试探,阿宝则又因此不确信李李的意志,转而放缓自己的追求与进取之心,于是在小说叙述的双线交织之中,90年代的失去便跟70年代的失去串连在一起。如果说70年代之痛首先是因雪芝松开了手,那么90年代之丧则是阿宝心中生着狐疑,他的手握得不够紧,而待到李李遁入空门,再想“紧握”,却已没得握了: 阿宝一呆。李李也就转了身,独自踱进一条走廊。阿宝不动,看李李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薄,微缩为一只鸟,张开灰色翅膀,慢慢飘向远方,古话有,雀入大水为蛤。阿宝觉得,如果李李化为一只米白色文蛤,阿宝想紧握手中,再不松开,但现在,阿宝双拳空空。庵外好鸟时鸣,花明木茂,昏暗走廊里,李李逐渐变淡,飘向左面,消失。阿宝眼里的走廊终端,亮一亮,有玫瑰的红光。一切平息下来。11 紧挨着这段文字,《繁花》(简装版)中附有一张金宇澄自绘插图,画的是蓓蒂和阿婆化作两条鱼,由三只猫叼至黄浦江跳水不见的情形,这样一来,在文图相照的世界里,阿宝个人的爱欲史就呈现为一种“一而再,再而三”的莫名重复。我们可以将第一次失去的动因归于时代,第二次归于雪芝,那第三次呢?很显然,由玲子、丽丽等众人所持话语或观念而生的精神围墙,自视甚高的阿宝不但未能自觉突破,反而在不自觉中依循着。譬如置身90年代,中年阿宝越来越不敢相信这世上还会有“奇迹”发生,因此有所谓“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式的“先见之明”。拉康说,“主体的无意识即是他人的话语”12,委实不是虚言。更进一步说,因受种种历史与现实观念所限,阿宝最多只会期待“奇迹”从外部世界或他人身上发生,而未能让自己首先成为“奇迹”,这是其个人的无意识,也是其所属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在解释自己“与瓦格纳决裂”一事时,尼采曾言:“一个哲学家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限制’。他得凭借什么来征服他最大的难题呢?凭借他身上恰恰让他是其时代产儿的东西。妙极了!我和瓦格纳一样是这个时代的产儿,可说是颓废者:但只有我领会这个事实,只有我与之抗争。我心中的哲学家与之抗争。”13虽然阿宝有时也会自以为深刻,但他同尼采所期待的“哲学家”无疑相距甚远,而无论是在他与90年代的精神搏斗中,与自身的精神搏斗中,他终究表现为一个凡俗之辈,一个丢掉“抗争”的“颓废者”,他既未能从自己的某种无意识中醒来,更未能进行如弗洛伊德般的“自我分析”和尼采般的“自我克服”。无法想象更无法做到“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这是90年代阿宝式的“精神疾病”,也是其自我拯救或拯救他人时最为隐秘的心理障碍。《繁花》全书结束于一家超市里传来的黄安的歌:“……花花世界/鸳鸯蝴蝶/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在此之前,雪芝给阿宝打过一个电话,从而旋起了一小片爱欲悬念,仿佛阿宝有可能获得新的情感生活,但即使阿宝真和雪芝旧梦重温,也终不过是某种步法零乱的撤退与苟且,是个人与时代同构的自我废黜。当然,无论二人此后“温柔同眠”与否,在小说中,阿宝曾经执念于“美而且好”的爱欲对象的历史已经终结——李李的出家,同时也是阿宝堕入某种精神“死亡”的开始,这两个人,皆未能成为对方攀向“天堂”的“荷花根”,李李出家的真相,是一个人从现实“逃”进了庵堂,阿宝撤退的本质,则是一个人从梦想“逃”向了现实。事实上,《繁花》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结尾,即让阿宝与李李携手成功,如此,则整部小说中隐伏四处的那一更大的难题就会暴露出来:一个人获得一个“美而且好”的爱欲对象固然很难,但更难的是拥有一个“美而且好”的世界。也就是说,在90年代,即便拥有了李李,成年阿宝也还是无法彻底重构其“原初的满足情境”——那一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世界”同在眼前的生命情境,而这一“满足情境”才是阿宝的爱欲所在,也是他梦想最深的“奇迹”所归。如果面对这一难题,小说家又当如何讲述故事及其结局呢?是请阿宝和李李一道,竭力鼓荡起他们的自由意志,以微观的方式“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甚或兼以宏大的方式尝试去“改变世界”呢?还是两人也只能跟《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一样,不得不做“一个残缺时代里的残缺的人”14?抑或是其他面目?

《繁花》写到最后,作者金宇澄选择让阿宝绝念,死心,跟黄安写的“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相配,也跟沪生讲的“现在我退一步,只能求稳,求实了”相配,大家携手归于当代同一种市民生态,表面上可能形式各异,甚至别具一番另类气质,骨子里却都是跟身边的“世道”或“社会”同床共枕。在此,我们有必要抛出一枚精神分析学式的“问题币”,它一面刻着:人为什么会死心?它的另一面刻着:人为什么不死心?不用说,我们在朝着阿宝和方言同时发问。前文中我曾引述过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人的欲望是一种力图“重新建立原初的满足情境”的“精神冲动”。现在必须补充的是,在表述此一重要假设之前,弗洛伊德先写有这样一段话:“毫无疑问,精神机构只是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才到达了现在这种完善程度。我们可以回溯到它的机能发展的某一早期阶段。一些在其他领域证实了的假设告诉我们,精神机构的最初形式是为了尽可能免受刺激而保存自身,因此,它的结构最初遵循着反射规律,从而使任何作用于它的感觉兴奋能够迅速地传至运动末端加以释放。”15这是一段不容错过或小觑的话,对人类而言,“使任何作用于它的感觉兴奋能够迅速地传至运动末端加以释放”的后果意味着:一个人将在欲望上“无欲”,在情感上“无情”,在思想上“无思”。因此我认为,弗洛伊德《释梦》中这段被一笔带过的话语,很可能是他对自己又勘探了20年后才正式发布的“死亡本能”理论的一次静默无声的眺望。同时我认为,在人们——例如阿宝和方言——企图“重新建立原初的满足情境”的欲望之前或之下,其实还隐藏着一种更为原始、更为强大的“欲望”,即弗洛伊德在20年代和30年代反复勘探的“死亡本能”——“一种比它所压倒的那个快乐原则更原始、更基本”的“欲望”,一种从“无生命的物体开始有生命的那一刻产生的”,要求生命体“努力回归到无机世界的平静状态中去”的“欲望”。16在本文之外的一些著述中,我曾尝试将弗洛伊德“死亡本能”假说中的“死亡”一词置换为“忘我”或“销魂”(本文将主要使用“销魂”一词),以悬搁该理论中的部分生物学实证意味,而注重凸显其精神现象学层面的揭示功能。17如果说“死亡”一词首先是指向生命的终结,那么我所谓“销魂”一词则首先指人的心灵的固化,更确切地说是指人的反思的终结——它是笛卡尔所言“我思”(我怀疑)的反面,是人的精神的无机化。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精神的无机化”并非一定意味着一个人思想或理智的崩塌,反倒常常指向一个人耽于或止于某种(些)思或不思,从而放弃了精神上的变革与反动,以至成为即便“有思”仍归“无思”之人。同理,上面所说的一个人在欲望上“无欲”和在情感上“无情”,也可以表现为一个人因耽于某种(些)欲而至“无欲”,因耽于某(些)情而至“无情”。其终归之所,尽在“销魂”。这样,我们或许能将事情辨别得更加分明一些。无论是想“上青天”——希求“美而且好”的人和“世界”同在,还是要“温柔同眠”——如沪生所说的“退一步”以“求稳”、“求实”,阿宝的心灵栖止地或精神休歇处,也都无外乎“销魂”二字。“上青天”也好,“温柔同眠”也罢,实际都是阿宝抵达“销魂”的具体通道,同时也是既可能被长期坚执也可能被因故置换的“销魂”形式。还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阿宝为何会死心?答案在于:阿宝所死,只是他“上青天”的心,而比这“上青天”的心更幽深更强大的,是人的“销魂”的欲望,因此,只要“温柔同眠”也能使阿宝抵达“销魂”境地,其“上青天”的心就非不可替代之物。那么,方言又为何不死心呢?此处不妨再作一点略显激进的辨析:方言,这个失踪者和逃逸者形象,在其选择出走的历史瞬间,恰恰跟许多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革命者、宗教信徒、陨石般倔强的“过客”等同属一宗,皆可被归为渴望在此岸或彼岸抵达生命极乐境地的人类形象。“幻想某种奇遇,生活一下完美无缺了”,这正是这些形象共同的欲念中心,只是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其具体的表述不同罢了。可以说,在《给我顶住》中选择了“上青天”的方言,就是《繁花》中无法仅以“温柔同眠”而“销魂”的阿宝,对于“这一个”阿宝,坚执关山平口中所谓的“幻想”本身,成为了最高的“销魂”之道——至少在一时之内。但同时我们也需看清,即便如此,在方言身上,最大的支配因素亦非其对“幻想”的坚执,而仍是“销魂”。倘若方言的故事得以继续,并使人们看到他在失踪后的某地、某时,终于也埋葬了自己的“上青天”之心,就跟《繁花》中的阿宝和沪生一样,委实是不足怪的。所幸,方言是以一种其心不死的形象存在的,他一心想着要摆脱那种“又回到烂熟的人群和环境中”所产生的“就像一个刚越狱的囚犯没跑几步又被抓了回去一样”18的不快,而未见有撤退或转移的迹象。因此至少在文本世界,作为一个生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普通市民,方言以其令人诧异的逃逸行为向世人表明,在理想的欲望对象无从“现实化”之前,对“幻想”的坚执亦可以成为一种或长或短的生命燃烧状态,我想,这大概是王朔所谓“给我顶住”的意旨之一吧。很难说,彼时的王朔是在借《给我顶住》以铭心刻志呢,还是用它来保存某种从此别过后不复念的私人乌托邦情绪?不过无论如何,《给我顶住》都给90年代初的中国人存下了一份值得留意的精神档案。从“事后”看,失踪者方言的最大难题在于,无论终点是哪里,他总得下车,然而关山平说:“这世界到处都一样。他无处可去。”对于此种判决和追杀,着地后的方言又将如何应对?在写下“我们完全可以假设,精神机构确曾有过一种原始状态,其中欲望终止于幻觉”之后,弗洛伊德继续写道:“内部的贯注只有在持续不断时才能具有与外部贯注同样的价值,如在幻觉型精神病和饥饿幻想中,它们将其精神活动全部耗尽于其欲望的对象。”19因此,在生理性的死亡之外,不仅是方言的身体需要着地,其精神上的坚执也需要着地——在现实中获得最渴望的东西,至少是部分获得或者不断趋近,否则,方言就极有可能会像尼采般地“疯”掉,或者像杜拉那样“从健康的生活逃入病中”20,即“将其精神活动全部耗尽于其欲望的对象”,而无暇再跟现实进行所谓“理性”的周旋。在这样的后果中,精神病症的发作,便成为一个人抵达“销魂”之境的“非常”形式。更多的人,在方言离开的那座城市,已于更早的时候选择放弃对“理想”、“远方”和“完美”的热望,比如周瑾和关山平们,她(他)们的选择,与生活在另一座城里的沪生和阿宝们于同时或稍晚些时候所做出的选择同质,要么是转换成“求稳,求实”,要么是从“上青天”撤退至“温柔同眠”。比如一次游泳时周瑾和赵蕾的一段对话,就涉及到这种日益普遍化的生命情态: “你老实说,这就是你希望的——我是说你婚前想像的梦想的那种……生活?”“不,”周瑾承认,“当然不一样。我也没那么说,我只是说我想通了。”“不认为那种生活存在了?”“不认为。”21 再将之前引过的周瑾、关山平的对话同周瑾、赵蕾的对话放在一起: “你说有么?那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的、人所期冀的……”“我说不上,一般的幸福感受我想是有的。譬如我们……现在……” 经由上面两段对话可以知晓,一个人在自我认定梦想不可为之时,或自我尚不能认定梦想可为不可为之时,“理智”地选择放弃,并撤退进眼皮底下的“现实”的怀抱,便是周瑾和关山平们“当前”的“销魂”之道,他们个人的“精神无机化”形态,它既呈现出他们作为普通人在其所属时代中的保守性,也呈现出他们的激进性和难以克服性——“销魂”只能通过“销魂”来替代与克服。问题在于,周瑾和关山平们的这种“销魂”之道不仅仅是其个人的精神无机化形态,而且也是那个最终成为社会主流的精神无机化形态,因此,周瑾和关山平们的“撤退”,或许也正是整个社会的“撤退”。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个“销魂”者——很多时候也就是求“销魂”而不得者,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由无数“销魂”者编织而成的世界之内,可眼前世界,种种使人“销魂”的“资源”终究有限,因此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销魂者”之间的矛盾和争战在所难免,要以完全撤回“现实”的方式让众人各安其道,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

在此视野之内,贾平凹出版于1993年的《废都》就值得重读——尤其是跟《给我顶住》《繁花》放在一起。《废都》的一大功劳,在于它刻绘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之间“西京”城里各路“销魂”者面相。无论深刻还是浅薄,激进还是保守,伟大还是庸常,也无论快乐还是悲伤,激烈还是平静,短暂还是持久,人的心魂总要凝滞于某人、某物、某事、某状或诸人、诸物、诸事、诸状等之上,从而放弃继续反思的意志和行动,此乃世间最幽深也最广阔的事实。具体到无名“闲汉”周敏身上,单有“美艳女子”唐宛儿其实是不够的——唐宛儿所起的“销魂”功能只持续了一个月,从周敏到西京城后的所作所为来看,其心中更大的念想,是对无名者身份的摆脱,尽管他在笔记里写有这样的话——“我寻遍了每一个地方,可是到处不能安顿我的灵魂”22,然而想通过写作“弄”出些名堂,从而让自己在人、物、事等面前拥有更多自由——比如说上西京城文人展览中心的“中央大厅”亮亮相的欲望,已如巫术般地攫取了周敏的神智,使他因此不择手段,至于其“不能安顿”灵魂之说,及其常在城墙上吹埙的苦恼行为,只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后果,而非他的思想或追求有什么分外深刻之处。至于跟周敏私奔到西京城的唐宛儿,则是奔走于另一条“销魂”道路上的周敏,一心想要成为著名作家庄之蝶的夫人且由此改变自身命运的欲望,或者说一心想要通过缠绕、攀附于庄之蝶而成为某个人群中心的欲望,是唐宛儿魂灵之“销”的核心动因。而庄之蝶的夫人牛月清,则先是“销魂”于经营、守卫其庄夫人身份的行动——里面埋藏着各种名与利的纠葛,后来经清虚庵尼姑慧明“教导”,又“销魂”于“女人要为自己而活”23的时尚话语之中。放眼观之,不甘心一辈子侍候人的柳月“销魂”于其对某种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的热望与趋近,西京城“四大闲人”之一、书法家龚靖元“销魂”于赌,其子龚小乙“销魂”于毒。文史馆研究员孟云房迷恋气功和占卜术,精神上无任何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可言。尚贤路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对阿兰施暴,这是人借性和暴力而至精神的无机化;农药厂厂长黄鸿宝靠卖假农药暴富,乃“销魂”于金钱;西京市市长为在自己任内出业绩,竟提议在城东区开辟了一条“神魔保健街”,乃“销魂”于权力……因此,那个在小说中四下出没的收破烂老头及其疯言疯语,无异于道出了整座西京城“销魂”于虚假、废颓、无信仰和腐烂的实相。可以说,《废都》所绘,是一个总体归“恶”的“销魂者”共同体图景,小说所传递出来的种种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早有研究者进行过具体分析。问题是,在不澄清“销魂”对人的规定性,或者说不揭露“人是销魂者”这一幽暗而普遍的事实的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又如何能进一步去开启某种新的、立得稳、靠得住的社会想象?这些年来,所谓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社会公共性重建等倡导之所以无功而返,其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在如今的社会总体语境中,它们很难具有一种能让人抵达“销魂”之境的力量和强度,从而也就很难与功利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等展开有效竞争——首先是遭遇了实践层面的失败,然后是遭遇了话语层面的失败。唯有“销魂”能克服“销魂”,再有效的压抑与克制,也只是让人类的某些“销魂”热望暂且流淌于地下或游走于边缘,一旦它们重新找到机会,就会以各种形式如火山般喷涌而出。人类一切朝向恶与不义的“销魂”行为皆不可能被直接禁绝,而只可能被朝向善与正义的“销魂”行为所转化或改写。而人类文明中的一切禁止与解放,也都是在使人“销魂”或使人不得“销魂”的维度上,不断解决和制造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销魂”的界面,人的所谓主体性或自主性是无效的,一切可改革、可鼎新、可替代的,不过是“销魂”的具体路径或形式,而对具体的“销魂”路径或形式之选择与创造,正是人类彰显其自主性或主体性的唯一场域,同时也是人类创造美好未来或良善世界的大道所出。那么,人又当如何行走于这条仍在迷雾中的大道之上呢?其间的巨大难题或障碍究竟有哪些?譬如,文人庄之蝶那种非由自主的情色审美冲动该当何去何从?完全的“解放”绝对是灾难性的,因为围绕着各个欲望对象,“销魂者”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无从避免,在唐宛儿这里,是她的“工人”丈夫、周敏和庄之蝶,在柳月这里,则是庄之蝶、赵京五和市长的残疾儿子大正,并且还有由此而起的牛月清、唐宛儿和柳月等人之间的争战。而在更加广大的人群之中,这种或公开或隐秘的色欲之争亦是无处不在。面对这一巨大的难题,最有效的解决之道也许是科幻式的,在未来世界,人类或可用技术手段去化解美的欲望对象的资源性匮乏,或者,用高科技的虚拟手段和脑神经刺激,直接使“欲望止于幻觉”,但也很有可能,某种新的不满足又会因此而起。即便将美的爱欲对象争夺战暂且搁置一边,而只讨论由两个爱欲主体所形成的微型共同体的内部生态,在《废都》中,庄之蝶的情欲释放也存在着严重的亏欠。比如说,庄氏的此类“销魂”行动基本上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多数情况下,其欲望对象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把玩、使用的位置,而非如小说中所说的被“创造”的位置,这固然跟叙事者的意淫冲动有着极大干系,但它同当时一些所谓文化名流的自我中心主义习性也有着极大干系——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自我中心主义也是许许多多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者所共有的精神内核,他们的理想也好,浪漫也罢,骨子里不过是其主观意志的膨胀与扩张罢了,在这一点上,《给我顶住》里的方言也不例外,他所希望的“奇遇”,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式的“奇遇”,在此“奇遇”中,无数他者只会是其个人意愿的幻化之物,而无法拥有其应有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现实处境中,许多时候自我中心主义也确实比操持他人意识和对话精神更容易让人抵达某些局部的、有限的“销魂”之所,尽管欢场散尽,虚无依旧。而像庄之蝶这样的文人,对此又一直缺乏某种警惕心和批判意识。要知道,对肉体快感的沉迷并不会导致庄之蝶对唐宛儿和柳月的真正败坏或“毁灭”,真正败坏或“毁灭”的根源,恰恰在于庄之蝶私藏在肉体狂欢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然唐宛儿和柳月们的精神实质,实际也不过如此。为什么这几个人的爱欲行为无法成为一种能让人凝神以视的爱的风景,更不曾让他们在爱欲中创造彼此的新生,结果反倒成了彼此间的败坏,使大家都沦为精神上的“废物”,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甚至还可以料想,一旦爱欲双方陷入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相互使用和彼此吞食,而非主体间的彼此创造和相互生成,那么《繁花》中阿宝最终朝向的所谓“温柔同眠”,就很可能会是一种消耗型的“温柔同眠”,其结局,便是爱欲主体在精神上的共同破败和腐烂。最后,当爱欲对象被“毁灭”之时,或者当爱欲对象离开主体之时,类似庄之蝶式的精神苦闷与灾难便降临了。然而多数人选择的救赎方案,往往是重复旧有的历史,即一如既往地寻找和消耗新的爱欲对象,其结局,通常是新的败坏。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曾忘记,《废都》中还有周敏们对“中央大厅”的无限渴慕,还有西京市市长们对权力的黑暗经营,还有洪江们对金钱的膜拜与热爱,包括庄之蝶们对成为经典作家的野心,及其对时时处处会有美艳女子献身于己的意淫与狂想……这诸多难题,无不需要人们站在新的思想地平线上,去勘探、开辟新的解放之道。而在这条通向无穷远方的集体航道上,方言、阿宝和庄之蝶们所乘的舟楫,似乎尽皆隐没了。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小微化青年形象谱系研究”[编号:2015BWY006]的阶段性成果)
1 王朔:《给我顶住》,《花城》,1990年第6期。 2 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442页。
3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高申春译,中华书局,2013年,第472页。
4 金宇澄:《繁花》,第13页。
5 此处所言之“美”,是指欲望对象在感性形式上的动人;此处所言之“好”,是指欲望对象在伦理层面的动人。
6 金宇澄:《繁花》,第295页。
7 同上,第333页。
8 同上,第371页。
9 参见吕永林:《罗陀斯的天光与少年——从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而来》,《文学评论》,2016年第5期。
10 金宇澄:《繁花》,第407页。
11 同上,第427页。
12 [法]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75页。
13 尼采:《瓦格纳事件·尼采反瓦格纳》,卫茂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14 陈染:《私人生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7页。
15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472页。
16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2-23、47、69页。
17 具体可见吕永林:《个人化及其反动——穿刺“个人化写作”与1990年代》,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三章;吕永林:《事关未来正义的正义——从蔡翔新著〈革命/叙述〉而来》,《上海文化》,2012年第1期,等。
18 王朔:《给我顶住》,第64页。
19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第473页。
20 弗洛伊德:《少女杜拉的故事》,丁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21 王朔:《给我顶住》,第60页。
22 贾平凹:《废都》,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193页。
23 同上,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