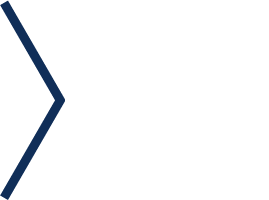关于 M 的音频采访节目1988 年,M 来到美国。和那个年代出国多数中国人一样,他凭借着全额的奖学金资助,在杨百翰大学学习社会心理学。但和多数人不同的是,他出国却是为了爱情。“我当时有个美国女朋友,所以很想去看看她生活着的国家,和她来自的文化。”
抵达美国几年不久,M 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博士。他得到了录取,却没有奖学金。1990 年的夏天,M 带着所有的身家来到纽约。一边刷盘子洗碗赚生活费,一边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努力争取奖学金,却迟迟没有着落。开学日的前一天,就在 M 做好了推迟入学、打一年工赚学费的准备时,竟意外收到学校的通知,“这里有一份在纽约心理咨询机构的工读奖学金,你的学费有着落了。”凭着这份来得太及时的意外惊喜,他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中国学生。来到美国之前,M 已经在国内大学担任讲师。在他自己的规划里,毕业回国,继续教书,一纸名校文凭在手,未来的职业生涯怎么都不会太差。“那时中国形势很好,大多数人都想在美国学习,之后回去建设祖国。当时的我一直都想回国,从来没想过要留下,”M 对我说,“我在国内的工作不错,我自己也喜欢教书,为什么不回?”* *和 M 认识,是因为我的一项移民新闻课的作业。我们第一次见面,在 H 大厦一楼的星巴克。1988 年懵懂的大学生,如今已经是 H 银行在纽约的副总裁。1994 年至今,这是 M 的第五份工作:频繁的工作更迭发生在开始工作的头六年,他辗转经过密歇根、经过巴尔的摩,最后决定投身银行重回纽约。这第五份工作,一做就是十五年。对于 M 来说,工作似乎从来都没有办法成为他生活的中心,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干这个,是为谋生,用时间和生命换取自由。”M 最热爱的事是教书,而今天的他和这爱好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在教会的语言班教中文。“语言是一个问题。学文科的,英文再好,肯定也不如本土,面对特别深奥的问题也会不如意。”M 回忆说,“我大学毕业那会儿,刚结婚、有了小孩。我太太是学习艺术的,没有出去工作,所以我迫切需要一份工作养家,正好有个机会,就入了金融这一行。”M 热衷户外运动和旅行,这留给他和职业不相称的黝黑皮肤,以及风吹日晒后疏于保养的粗糙;临周五,他会穿着条纹帽衫和宽大的休闲外套去公司上班;天气好的时候,做完当天的工作,他会开着车去山里爬一段山路。无论如何,M 看上去都不像是一个金融工作者:和商务人士身上精明、得体、进取的性格比起来,他显得温吞又随性。“既然没打算留下,为什么最后还是却留在了这里?”我问 M。本来兴致高昂讲述着自己生活的他,突然沉默下来。在我的注视中,泪水竟然夺眶而出。1989 年的夏天,M 每天都和一群留学生聚在一起看新闻度过。“和我一起看电视的一群留学生全都痛哭流涕,一个山东大小伙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真的,我们谁都没想到。那时候我就知道,回不去了。”1990 年 4 月 11 日,时任美国总统 George·H·W·Bush 签署了第 12711 号总统令(Executive Order 12711),规定“暂时禁止将 1990 年 4 月 11 日之前抵美的中国公民及其亲属驱出境,给予他们有效期至 1994 年 1 月 1 日的工作许可,免去居住满两年的要求”。1992 年,时任美国联邦众议员的加利福尼亚州籍民主党人 Nancy Pelosi 提出关于中国学生的保护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简称“CSPA”),给予所有在 1990 年 4 月 11 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人永久居留权。 这是一个在美国本土争议极大的法案。有人认为这样的保护并不必要的,有人认为法案的实际受惠群体远大于其最初目标,而一些非法移民也借着这个法案取得了合法身份。而在另一群海外华人的口中,在这个时期搭着政策便车而获得的绿卡被称为是“血卡”。第 12711 号总统令公布之后的几年里,约有 54,000 名中国公民因为这个法案获得绿卡。M 正是这 54,000 人中的一员。某一个无人可以推理而出的历史事件,改变了 M 和其他 53,999 个人的一生:原本规划设定的未来轨迹被生生折断,意外滑入了另一种人生。M 匆忙起身去已经休业关停的柜台,找一张根本不会有的餐巾纸,而我则像个做了错事的人,低头在什么也没有的背包里翻找一张不存在的纸巾。看着一个和我父亲年纪相仿的男人毫无征兆地哭出来,我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
纽约曼哈顿 42 街的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是全世界最多游客造访的景点。然而,对于数十万往返于于纽约上州、康涅狄格与曼哈顿的纽约客来说,中央车站是某种功能性、而非观赏性的存在。拥挤的站台、深邃的地下隧道和纵横交错的铁轨,这些他们生活无法剥离的一部分,比高挑的穹顶看来更温暖亲近,毕竟是这延伸的铁轨每天送他们去到想去的地方。他们每日清晨如潮水般涌入城市、傍晚,行色匆匆地和无数人擦肩而过,最相熟的是火车上检票员的脸。在 1948 年写给《假日》杂志的纽约城志《这就是纽约》里,E.B.White 甚至充满成见地描写了纽约的通勤者。“通勤者是最怪诞的一群了。他居住的郊区没有活力可言,不过是白日终了时供他歇息的地方。除了极少数例外,他们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仅限于火车或汽车班次,或者午间的快餐路线。他决不会在纽约闲逛,突然发现点什么,毕竟,他得忙着赶火车。他将钓丝瞄准曼哈顿的钱夹子,起获点小钱儿,顾不上倾听纽约的呼吸,也不曾清晨随它醒来,夜里又伴它入梦...通勤者生前,跑了不知多少里程,但他从来不曾漫游过。他们的进出路线,要比土拨鼠群落更迂曲,困在东河隧道的泥浆里时,听天由命地打桥牌。”
M 就是这潮汐般庞大人群中的一员。他工作的地点在皇后区科特广场 1 号(One Court Square)—花旗集团大厦,如果能在五点钟准时下班,他刚好赶得上五点四十分从中央车站出发的绿线火车,沿着哈德逊河一路向北 30 分钟的欧文顿(Irvington)是他的公寓所在地。沿途蜿蜒开来的哈德逊河的湖光山色,让旅程一点都不难熬,尤其是天气好的秋季傍晚。然而他很少能看到这景致—通常他离开写字楼的时候,早已是夜色深沉。往返中央车站与欧文顿之间的火车上,并不匆忙的一小时,是他固定的写作时间。在这被切割成碎片的时间里,他写自己喜欢的诗歌和散文,去年夏天开始写自己的第二部小说。M 家的墙上,挂着他旅行时拍的照片,每一年都会有几张 M 拍摄的照片被送去参展,“这一张是在印度拍的,那一张是在我家附近的公园拍的,这些都是刚从展览上拿回来的,”他一边随手指着墙上的画,一边对我说。M 是个音乐爱好者,最爱古典乐,书架上整齐地排满了贴好标签的 CD, 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古典乐当作背景音。他还喜欢逛博物馆、看展、听音乐会、看歌剧,每年都会和秋冬他都会和艺术家太太一起去音乐会和歌舞剧,“我太太不出去工作,她看得比我还多,去年一年她看了 15 场”。M 喜欢自然风光,常会和朋友一起在哈德逊河上泛舟、爬山,或者在自家阳台上远远看着哈德逊的落日。这些,是把 M 留在纽约的几乎全部理由。文化大革命、恢复高考、考取奖学金去往美国读书,M 的一生发生过许多意外,有些能分明地讲出好坏,另一些则是作为既成事实地出现,通常人们把它称之为“际遇”,这些大大小小的偶然叠加在一起,推着一个小小的个体走向一条远超出个人命定计划的路上。M 缩影了一代中国移民的故事:经历过七十时代的狂乱,感受过八十年代的希望,最终又被打碎。时代的冲击和创伤若非亲历,大概永远没办法感同身受,就像我面对 M 泪流满面时的茫然一样。颠沛流离之后,对安稳和平静的追求,最终超越了其它所有需求。家人和孩子、一台车、一栋房子、 一只宠物,典型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成为了 M 对生活的最高构想。“我在离纽约两小时的山上买了栋房子,如果哪天辞职了,我就搬过去。”“自由地漂流世上,在路上。有了家,有了孩子,就要有居所。我和我太太对物质的要求不高,”M 说,“之所以想搬到山里去,是想辞职以后,可以用最少的花销维持生活。纽约的花销太高了。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去山里花销会小很多。”“现在想回国吗?”最后我问 M。M 想了想,对我说,“父母都已经过世了,现在我的家人在美国,也没有特别要回国的理由。其实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过好当下,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好吧。”— END —
胡同阿伦特
VITA ACTIVA
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期待某些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