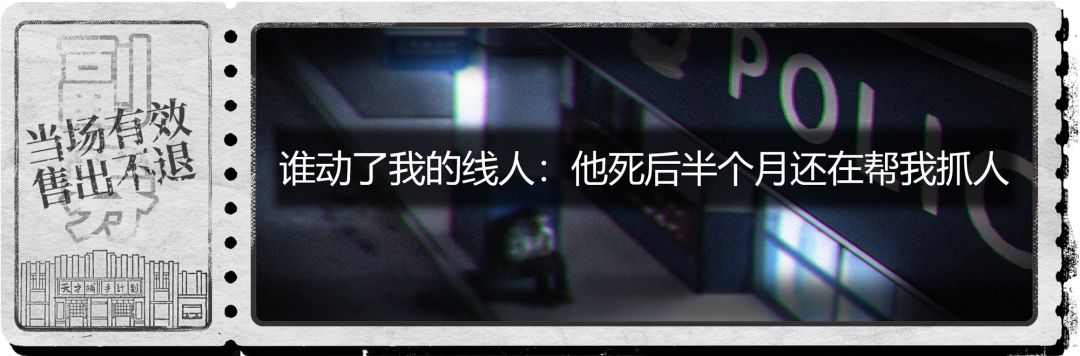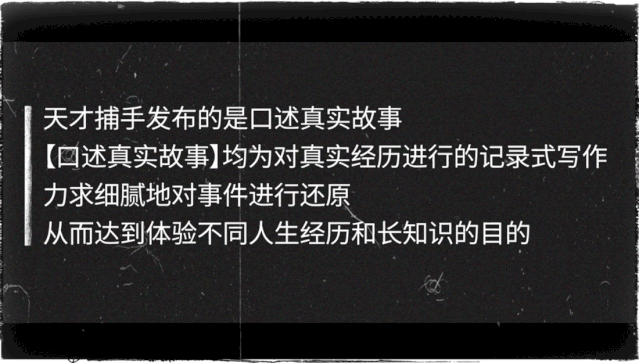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民间有个说法:新人手壮,第一次总会有好彩头。
但对一些特殊职业来说,这句话无异于诅咒。我听说过不少事例:
有个新手医生,职业生涯第二场手术,就遇上医院里几十年一见的罕见肿瘤。还有个心理咨询师,从业第一年就接待了一个老是念叨自己要杀人的客户,心理疏导失败,客户最后付诸行动。
今天的故事里,警察朱旭刚毕业就遇上了一件大案子,要抓一名特殊的杀人犯。此人居然敢掏出猎枪谋杀警察,闹得整个刑警队不得安宁。
当时,所有的老刑警都倾向于流窜犯作案,只有朱旭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没想到,真让朱旭误打误撞遇上了凶手,还差点儿把小命给交代了。

2017年1月27日,大年三十。小城里70多年历史的煤矿礼堂,迎来了最后的高光时刻。
春节后,煤矿礼堂将被拆除,原本两万多职工的大型国有煤矿也将破产重组。
煤矿礼堂曾经何其辉煌。足有十几米长的舞台上,聚集了小城所有的重要事件。最鼎盛时,半包围舞台的三层看台要容纳一千人,后门出口总是挤满抢不到座位的观众。
小时候我常和父母来这参加各种团拜会。当年礼堂甚至能请来唱“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杨洪基,还有在春晚上说相声的大兵……
如今,看台只剩下一层,木制阶梯座椅换成不锈钢架子加塑料。辉煌早已不在。
那天是我们分局的春季联欢会,不值班的人都到场了,台下黑压压满是警察。就连退休的前辈们都穿上洗得发白的89式绿警服,早早坐到前排等候着。
就在开演前,我们的局长郑舟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费力指挥着我用手机给他拍照。
背景是他精心挑选的,正好将一片磨掉漆的木地板纳入镜头。整个礼堂,只有这个角落还保留着过去的痕迹。
两个多小时前,郑局长就罕见地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开着帕萨特出现在我们派出所,一身板正的警服,冲进值班室就把还在值班的我拽了出去。
煤矿礼堂也见证了郑舟所有的青春岁月。他告诉我,“以前参加最多的就是公审大会。”
印象最深的那次公审大会发生在二十年前。2001年10月那天,30出头,刑警队“尖刀”侦查员郑舟坐在公检法、政府、工人代表们的身后,挤在人群中。
那天公审12名罪犯,郑舟不关心别人,只等着最后出场的——那个杀人犯。

2000年7月的那天凌晨,连绵数日的小雨终于停了。天蒙蒙亮时,李家岗居委会后面的小巷里,一个中年妇女瘫坐在门口失声痛哭。
这里是典型的棚户区,到处是一个小院两间瓦房的南方民居,不到一米宽的小路并着臭水沟曲曲折折地向远处蔓延,满是泥泞。此刻,除了闻声赶来的邻居,人们还在睡梦中。
那位妇女身后的小院深处,弥漫出一股淡淡的臭味。
白色“昌河”警车赶来了,负责大案要案的刑警二队来了几个侦查员——唯独少了“尖刀”刑警郑舟。
两年前,同样是雨停之后,同样是一起命案,一时冲动的郑舟拎着九七式微型冲锋枪抓捕嫌疑人,开了枪结果抓错了人。郑舟因滥用强制措施,被贬去了郊区派出所。
这个清晨命案中,顶替郑舟空缺的,是刚从沈阳刑警学院毕业,不过23岁的新人——朱旭。
他是当时整个刑二队最年轻的侦查员,平常密实的头发三七分,瘦高白净,一脸稚嫩。
刚从值班室床上爬起来不久的朱旭此刻顶着一团鸡窝头,打开手电,光柱在院子里晃动。
他走进门开着的那间。白瓷砖上洒满了血。家具上洒满了血。血迹已经发黑。一个姑娘躺在茶几和床中间的地上,手捂着脖子上的两个血窟窿。
她死的很痛苦,应该是捂着伤口挣扎了好一会儿。
室内除了几个酒瓶子以外,只有被翻遍的乱七八糟的柜子与倒在地上的尸体。“这是典型的入室盗窃转化为抢劫杀人啊!”年轻警察朱旭心想。
朱旭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弯下腰摸了下土灶台,冰冷。再看看锅里,一股馊味。
死者27岁,女性,名叫小燕,本地人。她常年在深圳打工,刚回家一周,还没走访过亲戚朋友,却倒在了血泊中。
法医判断,小燕大约死于两天前的凌晨时分,没有性侵痕迹,脖子上那两个血窟窿就是致命伤。
老法医拍完照片走出屋子,取下橡胶手套收拾家伙事。他满脚粘的都是发黑发臭的血污,走路黏呼呼的。他看着朱旭在院子里踱步,十分不快,嘟囔了一句:“不懂规矩。”
同行的老警察赶紧招呼朱旭去买瓶二锅头。这是警队老传统,看完尸体的人都要用高度白酒漱嘴,然后一口喷在手上。据说能消毒辟邪。
刑二队的人围绕着小院转了一圈,小燕家后面是杂草丛生的野地,后墙附近发现了人为踩出的痕迹。那些东倒西歪的杂草里,还隐藏着点点血迹。
草虽然不深,但密密层层难以下脚,朱旭他们每踩一下都能惊起蚂蚱、蛾子四散而逃。
血滴将刑警们引向了十几米外的一大片杨树林。杨树林的尽头,是通往外地的省道。杀死小燕的嫌疑人,恐怕乘车逃跑了。
当年这里是未经开发的荒郊野岭,如今早已改造成了驾校。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一个神秘人将小燕家洗劫一空,衣服上还挂着没有凝结的血水,仓皇经过。
连日的小雨留给现场的证据并不多。但侦查员们还是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张巴掌大、几乎被小雨泡烂的纸头。
朱旭一眼就看出来,这是从一本电话簿上撕下来的,上面还用圆珠笔写了一串号码,蓝色字迹已经晕开,但清晰可辨。
殡仪馆的抬尸工来了。见惯生死的工人瞟了一眼小燕:“刚死200,臭了500。”
听到自己女儿尸体的报价,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派出所的老民警赶紧把老太太拉到一边,转身塞给抬尸工500块钱和一包烟。

“嗨,流窜犯,下车摸过去或抢或奸,完了上车跑路。”刚开车回到刑警队,朱旭就听到同事这样说。
发生了命案,一把手必须到场,老局长早上直接赶到刑二队听汇报。当年全区二十多万人就俩刑警队,一队接普通刑案,二队接重案。
老刑警们都倾向于,小燕死在了流窜犯手上。
现场提取到的纸头,上面的电话号码归属地是东北的丹东市。在逃跑的路上还不忘撕毁的东西,肯定事关重大,就算找不到嫌疑人也是重要的调查线索。
没人反驳,散会后各自干活,把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当成侦查方向——自从郑舟被踢出刑警队,刑二队已经很久没出“刺头儿”了。
当年“尖刀刑警”郑舟主办排污沟分尸案时,就栽倒在“刺头儿”固执的劲儿上。
他咬住一条线索不放,死磕一个吸毒鬼。但最终证明那个吸毒鬼子根本不是真凶,他只是存心为报复前女友,给郑舟下了套。弄的“尖刀”被“发配”郊区派出所,每天处理邻里纠纷。
眼看着刑二队的案情分析就快定调,就差老局长拍板安排人去东北了。没想到坐在一旁的新人朱旭忍不住站了起来,“刺头儿”再次出现——
“我在现场走访到了一些情况,还是有必要汇报一下的。”
新人朱旭说,走访调查时他听一个起夜的大妈反映:前几天听见小燕家有人吵架,一男一女骂得很厉害。虽然没听清楚他们吵了什么,但是非常确定吵架的绝不是本地人。
“男的说的是东北话!和电视里一模一样!”
“那不还是抢劫杀人,搞不好就是东北的,不算啥新鲜线索。”说这话的是队里的老刑警。老刑警一副说教样子,一句话就反驳了“新刺头儿”。
“师傅你听我说完。”“新刺头儿”不低头。
朱旭继续说,在走访另一个街坊时,对方给出了一个与流窜犯作案完全对立的细节。说看到一个面生的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挑着水进入小燕家,应该和小燕认识。邻居根本没在意他长什么样,只记得有挑水这么个事儿。
“尖刀”郑舟犯错这两年来,大家查案子都变得特别谨慎。局长其实也倾向于流窜作案,但“挑水的年轻人”实在搞不清,好歹是条线索不能大意,这让老局长很头疼。
小燕一年也回不来几次,父亲早年在矿难中丧生,回家也只是住在李家岗居委会后面的小院里,而母亲家则在居委会马路对面,除了母亲隔三差五来这里看一眼,小燕在家总是待不了几天就会再回广东。
小燕的社会关系主要都在深圳。听说她在那边的夜场工作,不说别的,就凭小燕的相貌,找百八十个恩客都不成问题。
这种人际关系复杂的受害者,要想梳理出一个调查的线头,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新人”朱旭才毕业一年,连出差办案都没有过。老局长想到可以让个老刑警带他去深圳走访一趟,算是给新人锻炼的机会。
如果能排除掉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局里也能更有底气地组织人手去东北重点摸排。
其实老局长心里有个最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在南方打过仗,和三教九流都能打上交道的,被“发配”调解邻里纠纷的“尖刀刑警”——郑舟。

老局长决定亲自去请郑舟。
第二天上午,局长只身一人开车来到郊区派出所。他想让郑舟陪着朱旭一起去深圳,正好借这个机会,把已经接受了两年惩罚的他调回刑警队。郑舟应该重新做他最擅长的事情。
俩人见面的时候,郑舟正在为老大爷调节绵延了好几代人的土地纠纷。他喊来一边的联防队员继续调解,自己赶紧迎上去敬礼。大热的天地和老大爷算陈年旧账,他的嗓子都哑了。
局长示意郑舟把手放下,招呼他到楼上会议室,介绍案情。
“我都转业十年了,南边什么样了我哪儿知道,再说了,所里也缺人。”不出意外,郑舟直接拒绝了老局长重回刑二队的提议。
这时候派出所所长提着水瓶走进了会议室。所长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态度毋庸置疑:农村派出所穷得叮咣响,根本没有新警愿意来这受苦。好不容易调来个“尖刀”,哪有轻易放走的道理。
“尖刀”额角有道延伸到眉毛的长疤,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留下的。他一米八八,浓眉大眼,敢冲敢干,就是当警察的料。“尖刀”虽然鲁莽了些,但在同行眼里,绝对是个宝贝。
老局长也是军人出身,他知道郑舟还在因为被踢出刑警队的事情生闷气。那事儿对他的处罚确实重了。
郑舟当时心里想:刑警队因为这事让自己背处分,碰上棘手的案子才想起还有自己这号人能干活,让人心寒。
“我早就被局里忘了,然后等二十年后在这破地方退休吧。”
“小朱才毕业,你在一边照拂着我也放心,就当是老兵带新兵。”局长没有把案情讲得太细,他赶紧换了一套说辞,安抚郑舟的情绪。
“得了吧,我之前的那事队里早就引以为戒了。你们肯定不知道给新来的那个小朱说了多少遍。现在再让我去带他?人家估计打心眼里就不服。”郑舟想。
“这就是个劫道儿的案子,给新警练练手也好,对不住了局长。”郑舟说得很客气。
请郑舟出山的事情,失败了。

最适合办这案子的郑舟不出山,老局长安排一个快退休的老民警和一个联防队员陪伴“新人”朱旭南下,前后折腾了4天才辗转到达深圳。
那时候即使是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警察办案时都还没有执法记录仪和录音笔,朱旭他们外出查案,只能靠纸笔和脑子和两条腿。
“新人”警察原以为这就是个走访的活,如同自己在老家分局,不管要找社会混子还是红牌小姐,只要说个名字,社区民警一个电话就能把人叫来。
没想到,自己仿佛突然被蒙住了眼睛,啥方向都找不到——
2000年前后,深圳的酒吧、KTV、夜总会非常红火,从业者成千上万,而且大多是外地人,找一个叫小燕的女人,如同大海捞针。
“你睇,全国各地年年协查尸源的函件都咁厚,找你们这个女人,难度唔小。” 深圳民警用粤语味很浓的普通话泼了盆冷水。
当年从家乡出去打工的年轻女性有三个去向:河北保定、湖北武汉、广东深圳。从事夜场工作的女子,背后多有本地“鸡头”带领。
想找这样的女子,就要找到“鸡头”。朱旭这样一个新警察很难和这些人接触到,即使找到他们,对方也不会信任一个刚毕业的大孩子的。
那位深圳警察到是给朱旭提了个相当有用的建议:找在深圳混得不错的老乡,利用这层社会关系网,以人问人。这个在今天叫“人肉搜索”的玩意,朱旭已经提前十多年体验到了。
艰难之下,一同出差的老民警最终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圳某商会的副会长不仅是老乡,还是他辖区的人。副会长介绍了在酒吧一条街“混社会”的中年男子“阿青”。
“阿青”本是我省最北的社会混子,现在混到深圳酒吧一条街当“马夫”,粤语中马夫其实学名叫“介绍卖淫”。
“当时我才23,毕业不到一年,多多少少有些那个叫道德洁癖,自己是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人。但是没办法啊,人生地不熟,有求于人,只能硬着头皮上。”如今已经是副局长的朱旭说起这段往事禁不住大笑。
阿青一听说给老乡警察办事,一口答应下来。他接过朱旭递过去的照片,当时就脱口而出:“就是她!燕子。夜总会的头牌!”
原来,小燕没到20岁就来到深圳的酒吧一条街,在夜总会当陪唱公主。如果有客人要带她出台,她也接。
半个月前,小燕跟领班请假,说是自己母亲生病了要回家照顾。小燕不是一个人返乡的,在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小燕的男朋友陪着她。
“歌手是个东北小伙吗?”朱旭急着问领班。
朱旭根本听不懂广东话,只能让领班说一句,等深圳民警翻译一句。两人还时不时用粤语交谈一会,他只能在一旁干看着。
这段不长但是有用的信息足足聊了半个多小时,说到关键点的时候,朱旭实在是忍不住了。
“佢系广西人。”领班说。

当晚回到宾馆,朱旭几乎一夜没睡。
广西男人叫天宇,陪小燕回老家至今未归。朱旭在小燕家附近走访时,从街坊口中听到的那个挑水的年轻人,也许就是天宇。
他杀害了小燕之后逃之夭夭?但他是广西人,为什么说东北话?或者说天宇陪小燕回家之后就离开了,凶手确实是偶然闯进小燕家的流窜犯?
朱旭感觉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第二天一早,“新人”朱旭便把在深圳摸到的情况汇报给老局长。老局长在电话里半天没吱声。
朱旭说,这个广西人和小燕关系密切,应该就是小燕生前最后的联系人。不管怎么样,这人一定要找来询问。朱旭申请从深圳顺道去广西,到他老家进行外围调查。
局长沉吟了好一会,最后决定马上召集刑二队全体人员开会讨论。
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分局批准了朱旭的请求。局长特意在电话里说明:天宇目前仅仅是关系人,去广西只能开展外围调查,除非有确凿无疑的证据,否则不批准任何抓捕行动。
此时正值盛夏,朱旭一行人想想也没什么要带的,只简单收拾了一下。
临走前一晚,“漂泊”在外的一个“新人”,一个要退休的老警察,还有一个联防队员凑在一起喝了顿大酒,第二天三人就这么醉醺醺地上路了。

天宇的家乡位于广西西部的十万大山地区,靠近中越边境。朱旭他们先坐了一天火车从深圳到南宁,又要换乘大巴向深山进发。
此前,朱旭从没见过广西的风光,在长途大巴上看什么都觉得好奇。足足看了两天风景,朱旭只觉得到处都是一片绿以及时下时停的雨。潮湿闷热的天气让人心烦意乱,一趟车坐下来,衣服都是馊的。
离开深圳的第三天上午,大巴在县城里停车了。想到达中越边境的乡里,还得等私人承包的中巴车,就是既拉货也拉人的那种,而且什么点发车还得看运气。
中午朱旭他们在换乘站的小饭馆里喝了不少当地的米酒,正巧车也到了,大家就微醺着上了进山的车。
这里的环境比朱旭想象中糟糕得多,仅仅可以两车并排行驶的山路不知蜿蜒到哪里,时不时还有骑摩托或挑担子的村民迎面走来。
大巴里闷热酸臭,加上自己又喝了酒,朱旭在路上把脑袋伸出车窗,往外吐了不知道多少回。
山路的另一侧就是悬崖,路途颠簸,车里其他乘客毫不在意,一路上用广西俚语交谈着,但是朱旭被吓得心惊肉跳,有几次他觉得整个车几乎快要歪下去了。
朱旭攒了满身的臭汗,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下午6点多,终于到了。他们没敢停留,马上找到乡派出所。
天宇老家的民警听完了简要案情,先安排朱旭他们暂时住在所里,想下村还有很远的路,步行的3个多小时,等第二天白天才好走。
这里林子密度极大,到处都是高高矮矮的灌木。虽然朱旭的老家位于大别山余脉,丛林遍布,但是和广西的原始丛林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
天宇家的小山村只有30来户人家,除了一片被河流冲击出的小平原,其他地方非常崎岖。房屋依着高低起伏的地势修建,稍微好点的民居是上下两层的砖瓦房,差点的是看起来已经有些历史的竹木吊脚楼。村民的房前屋后种着一些作物,小鸡之类的家禽在村里乱窜。
村部也和这里大多数的建筑没什么两样,仅仅是一个二层砖瓦房,外面挂着一个党徽和村委会的牌子。
乡派出所的民警带着朱旭找到了村主任兼治保主任。那是个40来岁的中年人,虽然大小是个官,但是和普通农民没什么区别,也得下地干活。他已经有了白发,配合满脸的胡子,看起来不是一般的沧桑。
朱旭刚落座就给村主任递烟,又把寻找天宇的事情说了一遍。主任啧了一声,“你们和他回家也就是前后脚。”
三四天前,主任看见天宇从家里的吊脚楼出来,走进了不远处的大山,再之后就不知道了。说不定,人已经返回深圳。
“什么?人走了?”朱旭听完有些着急,忙问天宇家在哪里,还有没有其他人了。陪着他的老民警悄悄示意朱旭,遇事儿不能慌。
毕竟这趟过来只是摸清天宇的情况,就算天宇真的是凶手,也不能贸贸然地到处打听。走漏了风声,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办。
主任掐灭了朱旭递的烟,摸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往窗外一指,村委会对面那个竹子的吊脚楼就是天宇家的老房子,只有三间,家里除了房前屋后几片菜地,还有一笼子鸡。除此之外再没有值钱的家产。
天宇家和这里大多数村民差不多,每年的收入就是卖山货和地里那点收成,偶尔进山打点野兽,多少年都没有变化。
天宇从小就在村子大山的原始丛林里野跑,上完乡里的小学,等到14岁就出门打工去了。
当晚,朱旭他们回到乡派出所宿舍,打算第二天返程向老局长汇报。老民警总觉得哪里有什么不对,当时手机还不是很普及,他借了朱旭的翻盖电话打给深圳的老乡,让对方赶紧打听一下天宇到底有没有回深圳。
“我们从深圳过来,路上就耽误了3天。主任说三四天前最后见天宇,算一下日子,他应该已经到深圳正常上班了。”老民警计算着日子。
两个小时之后,深圳那边电话来了:天宇没有回去。

天宇最后一次现身,正在往大山里走。朱旭提出让主任带他们进山里看看。
第二天一早,主任带着3人进山了。临出发前,主任换上了一件老旧的绿色长袖军装,把裤管扎好,拿起一把弯刀。
他在路边砍了几根树枝,把上面的叶子和凸起削平,做了简单的登山杖。主任吩咐,山里面林深草多,拿棍子多晃晃免得招来一些小动物,“跟紧我,千万别乱走。”

上山的路只有一人宽,4个人排成一列沿着小路往深处走。朱旭身边到处是红色的土地、密实的灌木、裸露的山石上覆盖满了青苔,各种奇形怪状的昆虫时不时飞过,耳边是飞鸟一刻不停地鸣叫。
才走了几百米,朱旭基本就看不见路了。再走就只有护林员的简易窝棚了,传说附近有豹子出没。主任对他说:“就这样了,再想往里走得准备柴刀。”眼见也没什么线索只是在瞎逛,朱旭他们准备转身返回。
“嗵!”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响,余音在丛林里回荡。
“快跑!”响声刚落主任就大喊起来,嗓子几乎破音。
愣了一秒,朱旭看见不远处的林子里好像升腾起一缕白烟,附近的草木摇动,给人大事不妙的感觉。
顾不得其他,几个人跟着主任,玩命一般,用最快的速度下山,脸上、手脚上被灌木和锋利的草叶划出了好多道血痕。
朱旭很清楚,刚刚那一声巨响,是有人在对他们放黑枪。
跑出大山的几个人一边喘气一边互相打量,就好像在确认彼此有没有少啥零件似的。
万幸的是,大山里林密草深,山民惯用的前膛土枪也没多少杀伤力,铁砂被树木挡掉了大半,大家都没受伤,就是被吓得够呛。
几乎可以确定,偷袭他们的人就是天宇。

村里是不能待了。
本来这次南下,为的是走访了解情况,谁都没做好拼命的准备。如果天宇狗急跳墙,一个刚毕业一年的刑警、一个辖区派出所民警加一个辅警,根本对付不了。
大家一起去了乡派出所,朱旭把案情和盘托出。天宇的女友小燕惨死家中,此刻天宇凭空消失,最后一次有人目击是看到他进山。如今朱旭他们上个山都能遭黑枪,天宇畏罪潜逃的可能性非常大。
村主任十分震惊,他想象不到这个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可能背着一条人命。就算天宇这些年去深圳学坏了,他也还是个18岁的小伙子,怎么能杀人袭警。
朱旭显然还没有缓过来,他来不及弄掉浑身的草叶和露水,脚脖子上被划拉出来的血口子也没有治疗。他踱来踱去,无法平静。
老民警按着朱旭的肩膀让他坐下,顺手从他腰间拿过手机给局长汇报情况。
“操!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你们几个,赶紧给我回来…….”局长在电话里又急又气,让他们南下排除线索,竟然冒失到差点丢了命。
当着村主任和当地派出所民警的面被局长骂,几个人面子也有些挂不住,刚刚死里逃生的众人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在那愣着。最后还是当地派出所给了个建议:村委会,民兵还有民警都盯着天宇,只要发现他的踪迹就立即展开抓捕。
朱旭他们三个人取道南宁坐火车回家,一路上气氛沉闷,唯一的消遣就是买火车上几块钱一瓶的白酒,喝醉了睡,睡醒了继续喝。
回到刑二队,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三人被枪击的事情。同事们默契地没提这件事,局长也没有过多的批评朱旭他们。当务之急是,这个案子接下来该让谁接手。这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处理的了。
朱旭心里特别不好受。这次南下是他毕业之后第一次出差办案,他是刑警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还没来得及大施拳脚就快变成烈士了。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至少他提出调查小燕在深圳的社会关系是正确的方向。
“杀人嫌疑人大概率就是天宇了。”朱旭这样安慰自己,大家也这样安慰朱旭。
老局长的态度很明确,天宇凶残异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个亡命徒。他在山里东躲西藏,迟早有一天受不了苦要出来。没有经济收入,手里还有枪,这样的人早晚会继续犯案。
能抓天宇的人只有一个——郑舟。他从1984年7月起就驻防在对越前线,有丰富的丛林作战经验。
局长决定带着案子的全部卷宗,再亲自去一趟郊区派出所。
这次,一定要请郑舟出山。

新人朱旭一路南下调查只有他相信的线索,甚至辗转到中越边境的原始森林里寻找天宇。
这个第一次出差办案的新警察不知道,茫茫林海中,一杆黑枪已经瞄准了他。
敌暗我明,这次排查线索,不仅没抓到嫌疑人的影子,还让他差点丢了命。
这个案件的棘手程度,远远超出了朱旭的判断,也出乎了局长的意料。
看来,整个刑警队能够应付这个案子的,只有郑舟。
但局长不知道的是,郑舟曾参与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有战场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面对与当年战场相似的环境。
但这次,局长不想跟他好好商量了。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儿 扫地僧
插图:宋老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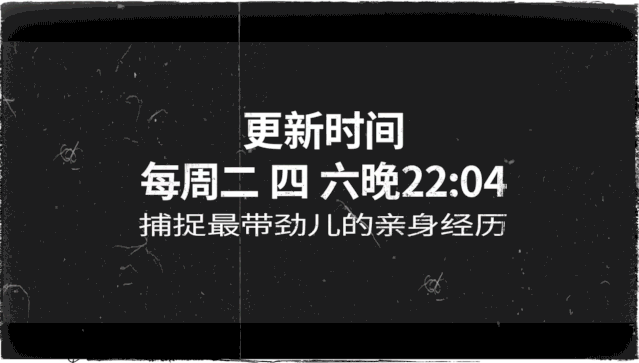
点击下面链接,观看更多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