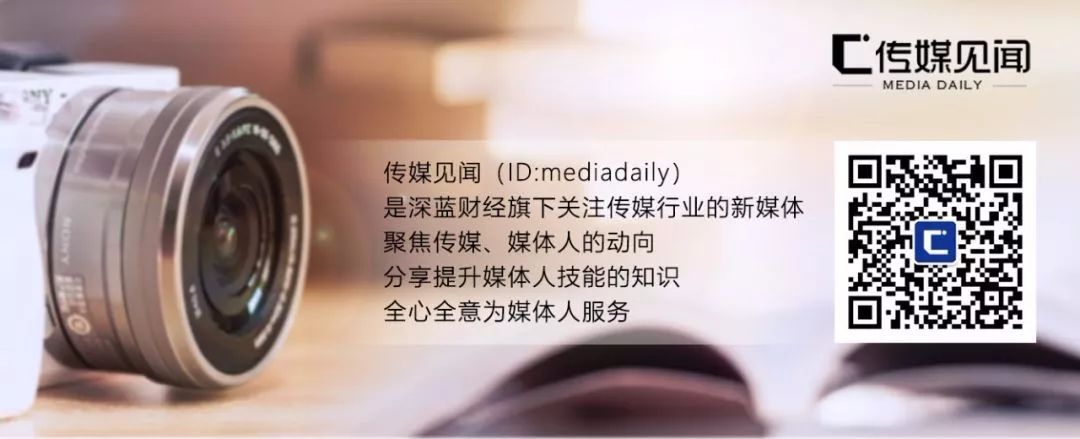媒体老司机——重温新闻老兵们的梦想故事,以及,他们重新出发的一些思考。


贾葭,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青年学者。历任新华社《暸望东方周刊》编辑、香港《凤凰周刊》资深编辑、GQ杂志中文版高级编辑、香港阳光卫视新闻副主编、腾讯《大家》创刊主编,现任外邦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十余年来,为内地、香港、台湾多家报刊撰写历史文化专栏,今年出版了讨论中国近代转型的新著《摩登中华》。

第一次失业,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些立场。
报社花了这么多钱,头班飞机,包车,成本这么高,稿子说毙就毙了。
很多优秀的评论者文笔其实都味同嚼蜡。
如果当时我能认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会继续选择做新闻。
你办的再风光,媒体大佬,总编辑社长,请问你占股多少?
媒体人转型通常是,做公号、做公司、做公关,做公公,做公主,做公益这六公。
和本期媒体老司机嘉宾贾葭老师见面,约在了位于成都北郊的戴季陶墓。
作为为数不多安葬在成都的民国要人,种种缘故,戴季陶的墓地鲜为人知,那天他准备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
以建筑、墓地描写作为开篇,是贾葭专栏文字的特色,最近他应《南方周末》的邀约,正在筹备一个讲述晚清民国人物的专栏,希望尽可能到每一个人物的墓地现场看看。
作为2003年入行,如今依然保持专栏写作的老媒体人,贾葭劝告年轻人不要进入新闻行业,在他看来这是一份不赚钱又十分危险的工作。
回忆起往事,讲述起身处新闻一线的作战经历时,贾葭又显得兴奋而开朗。
他非常感谢《凤凰周刊》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台湾和香港的政治,很多问题的看法都因此发生了变化。他也坦陈自己因为报道工作产生了新的兴趣,在社会百态中有了新的观察方向。
总之,媒体工作之于贾葭是段难以割舍的经验,而贾葭对于媒体行业也抱有热忱与喜爱。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离去。
如果当时能认清这些事情的本质
我不会继续选择做新闻
传媒见闻:记得您最早开始写专栏是看三联生活周刊,觉得那样的文字自己也能写,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贾葭:是的,那时候正好是非典期间。因为我大学期间读书比较多,杂志还是看的比较少,要做新闻了嘛所以开始看杂志,那时候《新闻周刊》和《南风窗》看的更多一点。
王小波原来在三联写过专栏,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类文艺类的杂志,没有把三联看作是新闻杂志,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三联办的不错,也是一本新闻杂志。有次在楼下的书报亭看见了三联我就买了一本看,当时翻开就看到那种短小精悍千字不到的生活小随感,觉得这样的文章好好写啊。
于是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照着页脚下的投稿邮箱发给了当时的栏目编辑苗炜了,一周就给登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实际上那会儿三联的稿子经常不够,苗炜自己化了好几个笔名在写。
传媒见闻:当时是已经开始从事媒体工作了吗?
贾葭:还没有,当时我是在光明日报。当时干的活是去找大学老师给那些自考的学生出试题,和新闻没有关系。
传媒见闻:这是您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吗?
贾葭:我最早是考了广电总局的公务员,但是后来没去。
传媒见闻:为什么考上了又没去呢?
贾葭: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就老希望我考公务员。内心我是不想考的,但为了堵他的嘴,所以就去考了,成绩还不错,进了广电总局,但我不愿意去。
传媒见闻:所以就没去广电,去了光明日报。
贾葭:对。
传媒见闻: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为什么要去《光明日报》做不喜欢的教育版呢?
贾葭:做什么板块的内容是报社统一分配的,我们没有选择权。工作热情也不是那么高,非典前差不多就已经辞职了。
传媒见闻:从光明离职后呢,又到哪去了?
贾葭:这就说来话长了,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一些立场,那是我第一次失业。
我离开《光明日报》是因为我和《21世纪环球报道》那边已经勾兑好了,我想的就是我一定要做记者,和连清川、沈灏都已经见过了,准备入职。结果就在我准备去报到的那一天,报纸被停刊了。
传媒见闻:停刊的原因是什么呢?
贾葭:主要是报纸采访了李锐谈改革开放。还有其他一些事,这样报纸被停刊了。
那是我第一次失业,停刊那天是温家宝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日子。当时有一个词语叫“胡温新政”,对于一个外省京漂青年来说,这个打击还是蛮大的。我在《光明日报》的时候一个月薪水就只有1500,21环球做的好稿费加起来可以到6、7000块,当时在媒体圈算比较高的了。
当我把个人经历和整体政治走向连在一起,有了一些思考。在我还没有开始做新闻的时候,就撞到了墙。其实后来我有想过,如果在那时候就明白有些东西是不可商量的,是不可抗力的话,我可能在当时就不会选择做新闻了。
当然这也是事后诸葛亮,很多年后,大概在09年、10年再回想我早年的经历时,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我能认清这些事情背后的本质是什么,我不会继续选择做新闻。
传媒见闻:您觉得这个本质是什么?
贾葭:我大概是在《凤凰周刊》工作的时候想明白了一些道理,说实话这个问题之前我并没有想明白,那就是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和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的是,不断的呈现观点和事实,然后拓宽大众舆论讨论的边界,让我们离真理更近,这样我们才知道个人和社会该怎么做选择。换句话说,不断地扩充言论的边界,我们才能知道中国向何处去,才知道路该怎么走。但是如果存在一些障碍,这个问题是得不到充分讨论的,所以我们做新闻,要不断地去拓宽言论边界,让大家参与讨论公共事物更广泛,更直接,更接触本质一些。这个道理我在03年时还并没有想通,觉得一家媒体被关了那我去下一家就行了。
传媒见闻:那下一家是哪呢?
贾葭:当年5月我就去了《文汇百花周刊》,是香港《文汇报》在北京办的一份杂志,主要以生活方式、文艺、软色情以及软暴力为核心内容,这大概是中国第一份讨论同性恋的杂志,同时还讨论中国人的性经验等问题,内容非常先锋,编辑都是当时媒体圈里最优秀的一帮编辑。主编是《看电影》的创始人尚可。
不过《文汇周刊》我也没呆多久,差不多10个月,2004年4月我就离开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可以真正做新闻的机会。其实也是偶然,那年3月底在一个饭局上我认识了当时《瞭望东方周刊》的张修智老师,吃饭的时候正好坐在我旁边。
整个吃饭的过程他一言不发,我很少在北京的媒体人饭局上看到有人这样沉默,他不说话就让我觉得这人深不可测,因为有的人一张嘴你就知道他是深是浅。饭局结束的时候,正巧我们俩回家是一个方向,我就问张老师要不要我打车带你?张老师就答应了。后来在车上聊,我只知道他是新华社的,就问张老师在哪个部门啊,他说在《瞭望东方周刊》,是一个新办的杂志。我就问他“你们还缺人嘛(哈哈)”,他说你有兴趣吗?可以来试试呀。我说“那什么程序啊”,张老师就问了问我过去的经历,因为我过去确实没有做过新闻报道,需要做一篇新闻稿给他们看看。
后来在4月份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篇稿子,作为我去《瞭望东方》的投名状。
传媒见闻:这是一篇什么稿子呢?
贾葭:当年6月,世界遗产大会即将审议中国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遗址。当时就觉得奇怪,因为在中国可申报遗产里高句丽并不出众,历史价值也未必大过其他备选,为什么中国政府偏偏要申报它呢?
带着这个疑问查资料,一查发现不得了。不仅中国在提出申请高句丽为世界遗产,韩国和朝鲜也在做联合申请,但高句丽遗址本身不在韩国境内,韩国纯粹是为了主张高句丽是他们的古代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朝鲜和韩国的立场是一样的,只不过朝鲜境内有好几处和中国境内那几处同期的高句丽遗址。
我还从一些学者那儿了解到,如果朝、韩申遗成功,可能会对中国关于高句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权定位有影响,未来朝韩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可能会有中国东北边疆的主权风险。所以为了防范这样的风险,中国在高句丽上报申遗的资料里面,将其描述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地方政权。但韩国和朝鲜认为高句丽从始至终是独立的,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只是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
当时韩国为了抗议中国申请高句丽遗址,在首尔举行了好几次抗议活动,人数众多,声势浩大。他们抗议中国侵占他们的历史。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它不仅是历史问题,还涉及边疆、民族、外交、文化等诸多问题,作为一个新闻选题,我觉得非常棒。通过研究看了大量的书才知道,中国在很早之前就给社科院拨了一千多万来研究这个事,叫做“东北工程”,那会这件事还没有激化,当时我觉得中国政府能有这样的魄力,还是很有远见的。
后来把这篇稿子交上去,当时的主编看了非常喜欢,觉得一篇稿子短短4000字就把这么多问题脉络能讲清楚,还通过学者提出了很多建议。结果到最后拍板的时候,因为觉得历史、政治还有民族问题这部分发出来不太合适,只留了申遗的部分,删了三分之二只留了1000多字。
传媒见闻:当时什么感受?
贾葭:我自己很不满意,因为我认为发出来的那部分没有显示出我的真实功力。觉得自己入职的时候,那些新同事要是看我以这样的稿子入职会看不起我的,后来我和老板讲我的忧虑,老板宽慰我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别担心。
传媒见闻:所以就这样在《瞭望东方》入职了。
贾葭:对,因为那篇稿子我就入职了。一开始是做时政新闻,但觉得兴趣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是新华社的杂志。
无力感初体验
传媒见闻:您在《瞭望东方》觉得不适应是因为觉得立场太鲜明了吗?
贾葭:这个立场是这样的,要理性建设性的提建议,有些报道方式我不太适应,就是用市场化媒体的方式讲述高层政治议题。我做过几篇这样的报道,比如政治局集体学习,比如李瑞环的哲学书,等等。有领导觉得这篇稿子拉近了领导人和老百姓的距离。过去的宣传可能更多还是开会、视察,讲出书的不多,我这篇稿子用市场化媒体的方式拉近了领导人和百姓的距离。
传媒见闻:但还是觉得兴趣不大。
贾葭:对,所以后来去做调查了。在做调查期间做的比较大的稿子是写新兴医院的。它是北京一家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有非常明显的莆田系医院色彩。当时还没有任何莆田系的概念,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北京有多少医院已经被民营老板买下来。我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知道了这件事情,我的一个朋友的太太去这家医院看病被骗了,他就和我抱怨说这可能是家骗子医院。我就和另外两个记者做了好几组报道。
后来这件事还闹得挺大,他们在央视的广告被停了,这哥们就天天拿着菜刀在办公室门口等我们领导。我还去他老家采访,发现这个院长以前还坐过牢。在他们老家采访的时候还被围攻,现在手臂上还有一个小的伤口,就是和他们抢我的记者证时发生冲突留下的。他们当时手里拿着镰刀,还好被警察保护了起来。
传媒见闻:还有别的令您影响深刻的报道吗?
贾葭:阜新的214矿难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情人节2月14号死了214个人,那一次采访让我知道一个记者原来需要那么辛苦,过去做稿子哪怕和别人打架也没觉得辛苦,但那篇做起来非常的辛苦。
矿难是下午发生的,但晚上消息才传出来。老板半夜两点钟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头班飞机去沈阳,然后从沈阳去阜新。我6点钟去首都机场,那天北京下大雪,没有一个航班起飞。从早上10点钟开始陆陆续续看到了其他记者,那时候北京的记者还经常聚会都认识。大家一碰一问,发现原来你也去那儿的哈哈哈。
大家坐在机场,都不敢走,因为不知道航班什么时候能飞。李海鹏他们后来忍不住了,担心这样会丢新闻,要是再晚点全北京的记者都去了,大家就一起去了这样就没有优势了。我听说《南方周末》也很着急就给他们包了一个车,直接开车去辽宁了。我算了下,他们开10个小时,我还是等飞机好了,也安全一些。终于到了晚上10点,第一班到沈阳的飞机可以起飞了。我12点多落地了沈阳,下飞机直接打车去了阜新。
在路上的时候,老板就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说他查了路况,沈阳到阜新的高速公路封了,你们肯定是走的国道,国道上都结冰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让司机开慢一点,让我千万不要睡着了。我问为什么不能睡觉。他说如果我睡着了,遭遇了车祸是来不及反应的,只有清醒的时候遇到车祸才有足够的时间反应。因为那时候没什么经验,这些都是老前辈告诉你才知道。一路上他又打了好几个电话告诉我,他是真的害怕我睡着了。
大概是在4点多的时候,到了阜新。我就想要是我先去酒店安顿的话,说不定一会李海鹏他们就到了。
传媒见闻:那时还是比李海鹏他们先到。
贾葭:我是头一班嘛,然后又是包车到了阜新。我直接去了医院,冲到了病房,把已经抢救出来的矿工采访了几个。后来医院就来人把人往外赶了。
传媒见闻:知道有记者来了。
贾葭:对,就把病房给封起来了。天亮了我就被赶出来了。我就去找住地,当地最好的酒店是政府开的阜新宾馆,那会儿也比较倾向于住这样的店,因为接待领导的缘故会更加安全一点。结果去了发现,里面全住的记者,已经住满房了。
他们都是到了以后先去酒店,洗个澡眯一会再出来采访,我是先去采访了,结果回来后没我可以住的了。后来就找了一个洗浴的桑拿中心,在他们的床上睡了一会,醒了就去现场了。
但现场已经封锁了,我进不去了。但还是有人进去了,听说是新京报的胡杰穿了一件呢子大衣,夹了一个皮包,雇了一辆奥迪A8停在现场。他体型有些胖,直接对门口的警卫一句:“情况怎么样”,哈哈把警卫吓坏了。还有澳大利亚ABC的一位记者,是个北京人,去了附近的矿工家里买了一套矿工的衣服,把自己脸抹黑背了一套工具假装进去救人也进去了,还下到了现场带了摄像机。但是像我这样的白净书生,没办法做这样的乔装打扮,就没有进到现场。没进去现场,我去了政府发布会,会上就说现在不让记者进现场,一切以现场指挥部发布的信息为准,不能随意采访。
我后来去了一位遇难矿工的家里,家徒四壁,唯一发光的东西就是一个锅盖是亮的,可能是因为刚洗过。用的是老式的煤油炉,家里味道很大,孩子趴在炕上,说是因为没有棉袄不能下炕,到了这种地步。这位遗孀大概20多岁,然后和我讲了她和老公从山西到这打工,租的房子,一个月多少钱这些情况。结果走的时候,她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扑通就跪下了,她问我为什么本地人赔21万,我们外地人只赔7万,人命不应该是一样贵吗?过去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人命到底是不是一样贵这样的问题,突然这个问题抛出来就像电击一样击中我了,我就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城乡户口的这种差别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死亡都是同命不同价的。
后来我又坐下来和她聊了一会,觉得稿子差不多了,就想从赔偿这个切入口去写这个报道。当天晚上写完稿子后,老板和我讲这稿子不能发,被毙稿了。我就觉得很对不起那位家属,因为她和我敞开心怀聊了那么久。所以第二天我就去她家道歉,给了她1000块钱,我说是报社给你的,实在抱歉稿子发不出来。她问我为什么发不出来,我给她解释我只是前线的记者,没有发稿权。
那是我第一次遭遇完整的毙稿。报社花了这么多钱,头班飞机,包车从沈阳开到阜新800多块钱,成本这么高,稿子说毙就毙了。老板说这是统一的决定,不是针对你。
我事后去想这些经历,就发现实际上是处处掣肘,比如说从医院被赶出来,被指挥部通知只能用官方的信息等等都是。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个高度上,只是认为是地方政府的干涉,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职业是受到很多限制。
对不同媒体的差别
传媒见闻:您刚开始做媒体那段时间,对做媒体存在的一些状况普遍都认识不深?
贾葭:应该是的,至少我是在后来到了《凤凰周刊》后才把有些事情想明白的。
传媒见闻:怎么想明白的呢?
贾葭:像之前阜新的稿子被毙,我当然知道这是限制,但还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度上。当然陆续也看了一些政治类的理论书籍,慢慢就开始想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关系到底是什么。2009年从凤凰离开后,我就不想做新闻了,去了GQ杂志。
传媒见闻:您从瞭望走了是直接就去了凤凰吗?
贾葭:我先去了《新京报》,和我在瞭望做的事一样,做深度报道编辑,但是没呆多久就走了。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节奏,每天下午4点上班,然后开会,讨论选题和记者讨论稿子,收稿,编辑,上版,忙完就夜里2点了,然后再吃点夜宵回家,怎么也要天亮了才能睡觉。那时候经常是天亮睡,下午1点起床,4点就要上班,吃饭都不在点上,所以那段时间胃溃疡又犯了,就想找个理由离开。
当时有个记者写了一篇稿子,但被采访对象并不承认他们接受了采访。我是那篇稿子的编辑,我问记者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不能拿出来,因为拿出来就把信源给卖了。后来新京报就把这件事给扛下来了,更正道歉了,还把相关人员给问责了。后来这个记者就离开了,我就找了个理由,说我身体不好,想休息一下,同时也说我自觉不适合这份工作,就让我走吧。
传媒见闻:这样就走了。
贾葭:对,后来就去了凤凰嘛。凤凰虽然是获特许内地发行,也都是内地人在办,不过毕竟尺度还是要大一些。给的工资也没有瞭望和新京报高,但去凤凰我就是看中了凤凰的尺度更宽,更有发挥的空间。
2005年那会我和安替一起办《纵横周刊》,我在上面写台湾问题评论,而且之前也在《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上写了好几次台湾问题分析,在那个时候的媒体人里面,我算是比较懂台湾问题的,所以去凤凰就想做港台新闻。
后来在凤凰邀请了很多《联合报》、《中国时报》、《新新闻》里面这些台湾非常资深的媒体人写稿。我也经常去香港和台湾。
传媒见闻:台湾似乎缺少思辨性的媒体栏目,为什么呢。
贾葭:社会中有很多思辨的空间,公共舆论的表达渠道和方式很多,不一定要在媒体中,我觉得不算是大问题。
传媒见闻:从香港、台湾、大陆三地的经历中有没有察觉到媒体风格间的一些差异?
贾葭:香港的媒体更接近英国媒体,台湾媒体更接近美国。香港媒体保持了英国和民国时期媒体的老传统,喜欢夹叙夹议,观点就在报道中不怕表明立场,会用有评价色彩的口吻去描述一件事。台湾媒体是学美国,事实和观点分的比较开。大陆因为市场化媒体改革一开始也是学美国,所以也更偏向美国。
传媒见闻:这段经历对您往后的想法上影响大吗?
贾葭:影响非常大,因为你在那样的社会里呆过几天后,感觉是不一样的。08年第一次去台湾采访选举,我从罗湖过境到了香港后,就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放松感,后来问了好多人,发现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之前听他们说过境后一定要深深的吸几口气,我开始觉得很矫情,但真正当我自己从罗湖过境到了香港后,那种放松的感觉特别强烈。后来我在余英时的回忆录里也看到一样的表述。
在凤凰的时候经常和台湾和香港的媒体人打交道,觉得他们好有文化啊,经常用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词,后来大陆也开始用这些词了,比如“福祉”、“履新”、“杯葛”这些。得益于这段经历,我有机会很近距离观察香港和台湾的社会,之前这些认知都是书本里的概念,没有切身的体会。
虽然只是港台部分,但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内地土鳖记者大开眼界了。我意识到,因为凤凰尺度宽,才能做出好报道。那时候在中国媒体圈,好多《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媒体发不出来的稿子,他们都私下问要不要拿到我们这来发,所以我们接了好多这样的外稿。那时候让我知道了一个正常的媒体应该是怎样的。
没有挑战,所以要变化战场
传媒见闻:您似乎总是不停的变化战场,为什么要这样?
贾葭:因为觉得没有挑战了,只要没有挑战我就会觉得无聊。
传媒见闻:您从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做编辑,有什么心得吗?
贾葭:我从业没做过几年记者,更多的时间都是做编辑。所以我经常和别人说千万别介绍我是知名媒体人,因为我没写过什么名稿件,甚至知名的评论,有但也是后期了。但我做编辑就非常认真了,如何能用最简单的汉语把一件事情讲清楚,不论多复杂的新闻都要精心设计出一个结构,把记者的材料填进去成文。
很多编辑是直接把编辑的稿子看一遍,签版说可以发了。我会在记者出发之前,告诉记者要注意哪些方向,事情可能会朝哪些方向演进遭遇什么情况,提供预判,会在后方配合、牵制记者去做采访。我不认为记者的自主性有那么大。作为编辑,我要求写多少字就是多少字,以什么角度写你就怎么写。作为编辑,我是一个知道该怎么把一件事以更好的角度清楚呈现的人,你要尊重我的权力。
很多记者的稿子在我这都有非常大的改动,甚至要求他们重写,给他们一个大纲讲清楚第一个小标题写什么,第二个小标题写什么。我会详细的给出一个结构。这些都是我跟港台的媒体学的,一开始看见他们这样我还很纳闷,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新闻史,才知道其实编辑的权限是非常大的,很大程度上决定一篇稿子的走向。
传媒见闻:那您怎么看调查记者与调查新闻呢?
贾葭:做调查记者,只要那件事在那儿,到了现场你会问会观察,可以把事实拿回来。调查报道呈现事实就好了,它可能需要勇气、体力会遇到很多危险。反而我觉得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下,你怎么能把一个故事讲好才是更重要的。
传媒见闻:所以编辑应该是掌控全局的。
贾葭:有一次给实习生上课。他写了一篇关于大兴枪击案的稿子,他开篇写的“砰砰砰,沉寂的夜空传来三声凄厉的枪响。”然后我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让他告诉我为什么枪声是砰砰砰而不是Biu Biu Biu,他说不是一般都是这样吗?我就告诉他,作为记者如果你没有听到那个枪响,你凭什么就以为是这个声音。所以我觉得很多是基本功的东西,在新闻学院是学不到的。一定是在行业实践中学到的。
编辑既应该是决定菜谱的人,还应该是决定如何上菜和摆盘的人。一个好的编辑应该对远处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大的判断能力。有时候我不相信记者到了什么程度?只要求他拿回事实,让他把看到的某年月日几点什么位置什么事情这些素材给我,我来写稿子。大家拿到手就是同样的一根白萝卜,怎样做能让它味道更好,这是编辑要思考的。
传媒见闻:编辑要对于故事好看负责,那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好呢?
贾葭:首先是看材料,然后去看别的媒体的报道。因为深度报道基本上都是做第二、第三落点的报道,那你要判断该如何把故事讲的更深入,然后选择角度。大家对于同一件事,看到的角度都不同。就像我之前讲的阜新矿难,现场进不去,那我就换个角度,去谈中国在生产事故中同命不同酬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得到重视,那在以后的安全事故中再发生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就是看你能为这篇稿子赋予什么使命。
传媒见闻:您提到赋予使命,但在新媒体时代,可能编辑还需要考虑阅读量,这该如何权衡。
贾葭:在我做媒体时就有一个讨论,究竟该迎合读者还是引导读者。如果要迎合读者我去做软色情和暴力,打擦边球就很容易做。但在自由社会之下,新闻作为第四权所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不断给社会挑毛病让社会变得更好。
我们在做纸媒的时候并不在乎发行量和订阅量有多大,有一种孤傲的气节,我就这么写爱看不看。但到新媒体时代,你的内容就与你的定位有关,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媒体,什么价值观的媒体。秉持一些价值观的媒体并不是没有人看,问题在于如何在迎合与引导读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比如六神磊磊,既有态度,也树立了价值观,同时迎合了读者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传媒见闻:您写作从来不考虑阅读量。
贾葭:一定要去抓只属于你的那部分读者,因为不可能所有人对所有事情感兴趣。而且作为媒体人,不可能对所有事情都知道,这和个人的立场、价值观念相关的。流量是有商业压力的时候才考虑的事。
中国媒体一方面受到相关限制,同时又遇到了媒体的代际转换,双重打击,所以纸媒才衰落,传统媒体才这么难堪。很难评价这对于中国社会的伤害或促进有多大。因为公众号出现之后很多界限都模糊了,很多传统媒体的操作流程很难延续。比如很多公号,一些文章中“小编”这样的措辞,我就特别看不惯,因为编辑你自己都把自己矮化成“小编”了,那你的公信力从哪来呢?
传统媒体是中心化的传播,需要更专业、更懂内容和有靠谱价值观念的人来做。很多媒体存在的价值仅仅局限于考虑经营收入,对于公共和社会进步有多大价值很难讲。
传媒见闻:作为评论人呢?如何写好评论。
贾葭:多读书是肯定的,还有就是观点够不够新,有没有解释力。评论的功能就是贡献观点,我作为专业人士,这件事我是怎么看的,在新的观点下我提供了什么新的解释框架或者解释角度,让大众以后怎么去看这件事。
同一件事,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角度都可以切入,你需要提供不同的解释框架,让我们的读者更多的思考这类问题的进入角度和思考方法。因为读者不是专业人士,不会想到还可以这样看。
输入和输出也有不同,你看那么多书,如果不输出,就不能有效的整理和富有逻辑的思考。阅读、写作、思考是三位一体互相启发的过程,纯阅读就变成了读书人,不写就只是观念的了解,不能有更大的启发。如果只写作不看不想就成了纯文学。写评论要有学理的积累,有解释事物的框架,提供对一件事的解释力。
传媒见闻:所以文笔并没有那么重要。
贾葭:我给腾讯大家当时提了三个标准,价值、洞见、美感。价值是我们要有靠谱的价值观念,要立的住。洞见是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角度,要有解释力。美感就是文笔,是最次要的。很多优秀的评论者文笔其实都味同嚼蜡,文笔只是为了让你读起来很痛快,是审美上的享受,但是价值和洞见是思维上的享受,是满足不同需求的。
传媒见闻:您怎么看待媒体人转型这个问题呢?
贾葭:别做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创业另外两个合伙人都是移民行业的专业人士,我只负责做公号吸引流量。我非常坚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其实媒体人出路通常是,做公号、做公司、做公关、做公公、做公知、做公益,这六公。
媒体人为什么赚不到钱?
传媒见闻:您离开媒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贾葭:不赚钱还危险。
传媒见闻:后来去帮人移民。
贾葭:写稿子的时候,很少能感受到反馈,不知道对哪些人产生了作用,感受非常虚幻。做移民的时候我和我的受众面对面更直接,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成就感是可感知的、具体的。我的客户从澳洲回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礼品,描述他们的感受时,这种成就感非常棒。
传媒见闻:所以这份工作还是能给你带来成就感的。
贾葭:当然,因为我可以具体的帮助到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一个客户的小孩非常开心的过来说,谢谢你,我很开心爸爸把我带到日本读书。
传媒见闻:那有没有受到质疑呢?或者感受到一些外在的压力。
贾葭:移民是一个个体选择,是人对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做出的抉择,和公共事务没有关系,甚至是个人隐私。中国移民率本身就很低,欧洲移民率是3%,中国只有万分之1,所以横向对比我们的移民率非常低。有遇到指责,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传媒见闻:很多媒体人创业后,都觉得管理很困难,您有没有特别不适应的时候呢?
贾葭:管理对我倒是没什么困难的,管理是有方法的。之前在腾讯的时候就带过十多人的团队,腾讯还有针对主编一级的管理能力培训课,很受益。现在外邦也是十多人所以这个问题不大。感觉到难的就是发不出工资吧,投资人的钱已经花完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进账,有过艰难到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要不要借钱,要不要继续干下去,揪着自己的头发想明天要不要去宣布把公司关了,要不要给孩子们贷个30万给他们发工资。
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创业的过程中,你需要为每一个决策负责任。曾经因为一个错误的决策导致公司有8万元的损失,股东过来埋怨,我说我承担这个损失。可如果是80万呢?当需要为每一个决策承担责任的时候,才觉得负起决策的责任是很难。
传媒见闻:感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还是回到媒体行业比较好。
贾葭:没有。
传媒见闻:外邦科技现在的经营状况如何?
贾葭:我们还可以,早就自负盈亏了。
传媒见闻:那对于新进入媒体行业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贾葭:我不建议年轻人进入媒体行业,我从2008年就讲这样的话,告诉那些实习生能不进媒体就尽量不要进,去外企及大型民营企业。媒体又不赚钱又穷又危险。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媒体人不可能拥有这家媒体的所有权,当所有权不在于你的话,永远不能指望通过它发家致富。
产权是最核心的问题,北京为什么有很多胡同那么破败,因为过去不承认房屋私有产权,我作为住户自然没有动力去修缮它,如果这是我家祖祖辈辈可继承的房子,那我就会去修缮。为什么欧洲有300、400年的老建筑,就是因为他们保护了私权。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如果去查是能查到具体某人、某个家族、某个企业的持股比例的。国内的媒体,你办得再风光,媒体大佬、总编辑、社长,请问你占股多少?0!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清末民初到1949,从帝制到共和,由天下而国家,直至今日,这个转型仍在进行之中,我们依旧在这个大变局中。
贾葭老师新著《摩登中华》现已正式发售。
本书主要谈及清末民初到1949年之前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每篇文章都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建筑入手,采用娓娓道来的故事方法,带领读者从历史情境中进入这些重大问题。
购买贾葭亲笔签名版《摩登中华》请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
传媒见闻官方交流群现已开通,
请扫码添加小编微信(请注明单位+姓名),小编将邀请您进群~~